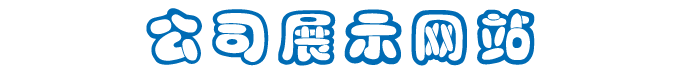
这些年文坛新闻热点之一,就是各作家、编辑和出版社,为配合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而动作频频,希望能在海外有所斩获。中国文学“走出去”从来就不是新闻。很多年前,相关的新闻报道一般集中在余华、苏童、莫言和格非等作家身上 这些年文坛新闻热点之一,就是各作家、编辑和出版社,为配合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而动作频频,希望能在海外有所斩获。要走出去和如何能走出去,当然涉及几个必备的条件,一是要有实力,这里指作家的实力,出版社对作品推介的能力;二是作家的作品能否被海外读者喜欢和接受;三是要知道如何才能走出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渠道,这涉及技术层面。作为中国作家的一,我对这个问题也颇为关心,近年又幸而有些实战经验,所以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和分析所面临的困难。 中国文学“走出去”从来就不是新闻。很多年前,相关的新闻报道一般集中在余华、苏童、莫言和格非等作家身上,特别是当他们的《活着》《妻妾成群》和《红高粱》等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在海外放映后,他们的小说也引起海外读者和出版社的关注,有了第一波冲击波。我那时候不了解海外的情况,以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很大。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刚开始小说写作不久,在国内发表都有一定困难,虽然也期待自己的作品能走出去,但当时属于“奢望”的事。作为一名围观者,看了无数热闹,对国外的情况也不了解,看报道就相信了,觉得那些事情距离自己千万里之遥。 我移居后,重回学校学习英语。有了语言和生活的便利,我对海外世界的了解慢慢多了,这有我最关心的世界文坛的信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的那年,我问我的英文老师斯科特(他也是电影导演)对此怎么看,他竟然说他不知道这个消息,这很让我惊讶。后来我渐渐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现状慢慢有了新认识,状况与国内的新闻报道有些出入。 2014年前后,有翻译家朋友开始翻译我的短篇小说。因为对海外英文文坛不了解,过程十分。我搜阅了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文字和视频资料,发现一个作家要在另一种语言下,的确十分。 哈金初始收获到的是源源不断的退稿信,以至于他有一段时间不敢在饭前查看邮箱,以免影响食欲。但他毅力惊人,经过不为外人知道的困难和努力才获得了今天的成绩。我他,也拿他作榜样。我拿着翻译家翻译好了的短篇小说去。这其实很不寻常,因为不会有作者自己拿了翻译稿去的,这个工作通常该由翻译家去做。但因为他们对英语文学也不了解,而且时间和精力有限,我只好代劳了。我花费几个月时间去搜索信息和寻找文学刊物,先从大牌开始,依次往下推移,我就这么干了,还线年发在《短篇小说》第9期的中文小说作《游戏的尾巴》,被翻译家孙继成和Hal Swindall (师文德,下同)译成英文,2015年刊发在有90多年历史的美国老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学》)第5期上,那是我初登世界文坛的英语作。之后,我给译介中国文学的著名中译英Renditions (《译丛》),它在译界的地位相当于《收获》。此前朋友说不可能成功,因该主要发表中国现代作家或1949年以前中国作家的中译英作品。我查过它过往的目录,的确是这样,但我还是决定一试,从2014年开始,终于在2018年5月发表了由杨晓文翻译的短篇小说Drifters (《自游人》),11月又发表由孙继成和师文德翻译的短篇小说 Who Flies In April(《谁在四月飞翔》),连续两期发表同一个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该刊一年两期),也算奇迹了。主编还给我写了一个邮件,希望多给他们稿子,让我十分受鼓励。 我在谈论的,是我当初走出去的情况,这些成功尝试,当然涉及作品的质量。此外,也说明作品适合海外读者的预期。小说不像诗歌,它更需要读者,没有读者市场的作品,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记得有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法。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翻译作品并不容易被海外读者接受。拿美国来说,出版业和读者都不喜欢出版或阅读翻译作品。据统计,美国每年出版的翻译作品仅占整个行业总量的2%左右。 我们常有一个错觉,以为中文是“世界语”,大语种,其实到了海外,中文就成了小语种,英文、法文和西班牙语才是大语种。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除了语言的因素,还有作品所包含的“价值观”的问题。为什么其他国家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发达国家的作家,还是第三世界亚非拉作家的作品,他们杰出的作品都能得到读者喜欢和接受,为什么中国作家的作品让人喜欢就那么难?有人归咎于翻译的失败,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因素而已,重要的还是你的“价值观”得符合“人类”的标准,而不仅仅只符合“中国人”的标准。我认为汉语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语言体系,可能造成一种交流的障碍——历史文化悠久造成了一种群体内的人可以“心照不宣”,而群外人则无法的尴尬语境。这需要作家在写作时,要有极强大的“沟通”写作技巧。 我被译成英文的短篇小说,原来大都发在国内二三线文学刊物上,译作时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凡我二三线的英文刊物全军覆没,而接受我稿子的,大都是大牌老牌英文刊物。这间接佐证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特定下,甚至是相反的。因为我的作品放在国内绝对算不上主流的。 我再谈点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就是走出去的渠道。现在国内的出版社有去海外设立分社的,有直接由国内出版社出版翻译作品的。国家对“走出去”项目也有资助。这些支持有好的一面,但也由此产生了现象。看新闻报道,某地作协与国外某出版社签订出版协议,一下出版8部英译作品;某著名作家获得项目资金资助,由的中文出版社一次出版6部英译小说文集。我还看到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China Channel(《书评中国频道》)上的一则书评,评介中国某著名畅销书作家的英译小说“翻译糟糕”,而该英译小说是由国内中文出版社出版的。 我们很努力去实践“走出去”的行动,但这样的做法效果堪忧。海外读者大多不会购买由中文出版社翻译的英文书的,因水准相当可疑。要出版还真的要由当地的英语出版社操作,他们熟悉了解当地的市场和读者阅读习惯,从而制定出最适合的销售策略,并为你作品的后续出版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上网搜索发现有些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虽然翻译出版了,但在Amazon网店上基本没什么销量。 如何走出去,如何能走出去,渠道很重要。这需要有当地机构代劳,这样的发行才有力度,宣传才有效果。拉美文学能如此繁荣,离不开著名的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Carmen Balcells ),她了整整一代拉丁美洲作家,其中就包括《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反观我国,竟然没有一家像样的文学经济公司。我一直希望有经纪人可以代劳这些出版琐事,我曾经联系上几个代理过中国作家的经纪公司,我和他们沟通时才了解到,他们有的是小公司,资源有限。有些则因之前代理的中国作家的销售业绩不太理想,以至于他们不愿再代理后续中国作家的作品。 现在,我的中文作品的翻译推介工作主要由孙继成和师文德两位翻译家在做,他们正在翻译我的短篇小说集,共有17篇短篇小说,先单篇发表,再结集出版。而我则把精力放在英文小说的写作上。选择用英文写作,既是寻找写作生涯的突破,也是挑战写作极限的一个方式。我发现在写作现实题材的时候,由于与“现实”距离太近而失去了部分“想象力”,而用英语写作,由于语言的“陌生感”而与现实产生了“距离感”,从而解决了“想象力”部分缺失的问题。 回头看自己实践“走出去”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当初只是朋友开玩笑对我说,用英文写吧,你对语言那么,又有前辈哈金等成功的榜样,你用中文写了半生了,不妨尝试后半生用英文写,或许有成功的希望。我还真就去尝试了。哈金先生在采访时说过,作家不能只有一部书,要有一排书耸立在书架上,这样才不会被人忘记。这话不但对他是个鞭策,对我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有人问过我,在没有文学经纪人的情况下能走出去,有什么窍门。我想除了对文学的热爱,对写作目标保持惊人的毅力外,还有相关朋友的支持。而从我的成长经历背景来看,我有比较完整的人生履历,小镇出生、成长,移居深圳并了其由小镇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去上海华东师大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回到深圳一家银行工作,后移居,有海外生活和教育经历,现在又返回深圳生活和写作。这些经历使我与海外读者的沟通没有障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更接近“人类”的标准。 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我在写作中国故事的时候,阐述我对当代中国问题和人生意义的追问时候,不会只把思考局限于中国框架内,而是会把它放在更广大的视野去加以考虑,这使得我的作品在“走出去”的上,被海外读者接受的程度可能更高一些。欲望情夜
|